
圖:香港山容海色兼?zhèn)洹?/p>
我愛(ài)讀書(shū),好行山���,還很在意一段“移植海隅”的歷史���。書(shū)���、景����、史����,三美兼具,唯在香港�。
家中長(zhǎng)輩曾在香港工作,本世紀(jì)初的十一年����,我每年都會(huì)訪港探親。家住灣仔�����,樓下軒尼詩(shī)道巴士嗚嗚,電車(chē)叮叮���。北有會(huì)展中心�、維港碧波����,南接綿延山道,西望金鐘���、中環(huán)���,穿鵝頸街市東行五分鐘即至銅鑼灣。
在軒尼詩(shī)道搭叮叮車(chē)�����,七八分鐘就抵達(dá)香港中央圖書(shū)館����。書(shū)架成排,書(shū)籍如林����,為保護(hù)圖書(shū)��,平裝本亦改裝為硬精裝�����,拿在手中����,平添敬意���。雖面向大眾,冷門(mén)書(shū)也不少���?���!禩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二○○二年于紐約出版�,香港中央圖書(shū)館翌年已上架。好奇“歪果仁”怎樣寫(xiě)中國(guó)文學(xué)史�����,我把這部墨綠封面、一千三百馀頁(yè)的“大磚頭”辛苦抱回家細(xì)讀���。曾想借一冊(cè)日文書(shū)���,電腦顯示在架上,卻遍尋不到�,去前臺(tái)咨詢。廣東話“識(shí)聽(tīng)唔識(shí)講”�����?無(wú)妨��,館員英語(yǔ)流利���,記下我的電話號(hào)碼��,次日來(lái)電說(shuō)書(shū)已找到����,即時(shí)可來(lái)領(lǐng)取��。還書(shū)��,只要走到軒尼詩(shī)道旁的駱克道圖書(shū)館,放到還書(shū)箱里就好���。
手癢想買(mǎi)書(shū)�,會(huì)展中心旁有家書(shū)店��,專售英文新書(shū)��。希拉里.克林頓的《Living History》二○○三年六月出版����,當(dāng)年六月下旬去香港,這家書(shū)店的顯要位置已擺滿此書(shū)����,書(shū)店玻璃墻外都看得到作者在封面支頤微笑���。搭叮叮車(chē)至上環(huán)���,幾家素樸的書(shū)店常有內(nèi)地早年出版書(shū)籍。二○○九年冬經(jīng)灣仔修頓球場(chǎng)�,遇臨時(shí)書(shū)展,折扣極狠�,立即買(mǎi)買(mǎi)買(mǎi):蔡志忠《漫畫(huà)中國(guó)思想》��、阿辻哲次《圖說(shuō)漢字的歷史》���、林達(dá)《近距離看美國(guó)》系列……
羅素在《Knowledge and Wisdom》中指出,人類(lèi)一如其他動(dòng)物���,看世界傾向于以“此地此刻”(the here and the now)為唯一中心��;而智慧的精髓�����,在于從此地�����、此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(lái)�。讀書(shū)����,幫我離開(kāi)“此刻”,上溯過(guò)往��,遠(yuǎn)瞻未來(lái)。行山�����,帶我跳出“此地”��,在四方上下的六合空間坐標(biāo)系中尋找芥子一粒的自己�����。香港正是行山寶地���。
水似眼波橫����,山如眉峰聚��。長(zhǎng)河寔美����,滄海尤佳���。依山傍海的城市如大連�����、青島����、西雅圖,美不勝收����。而香港之妙,在于山水與鬧市的無(wú)縫銜接�����。灣仔東����、北、西三面��,人喧車(chē)鬧���,而只要往南行����,數(shù)分鐘后已置身山中。沿灣仔峽道�����,一面是山坡�、花樹(shù),一面是漸行漸低的樓群和隱隱市聲��,一直行到香港仔郊野公園��,或岔進(jìn)寶云徑而抵中西區(qū)���,或轉(zhuǎn)入港島徑而西上山頂���。山道眾多,行人寥寥��,蟲(chóng)聲?shū)B(niǎo)鳴����,更助冥思。登山望海����,壯觀天地之間,體以行和�����,鬱以勞宣���。遠(yuǎn)足之妙���,香港惠我實(shí)多。
許多城市都有發(fā)達(dá)的公共圖書(shū)館系統(tǒng)�����。少數(shù)地區(qū)得天獨(dú)厚�����,山容海色兼?zhèn)?。而那段我在乎的歷史,別處所無(wú)���,唯在香港�。
軒尼詩(shī)道國(guó)華大廈�����,《大公報(bào)》舊址。我因好奇�����,曾請(qǐng)人帶我進(jìn)樓����。沒(méi)有保安,僅一“傳達(dá)”�����,編輯部向公眾敞開(kāi)��。七八個(gè)年輕記者�����、編輯正聚在一起讀著什么��,突然爆發(fā)笑聲���。每人一小電腦桌�����,桌兩旁立隔板�。同行之人指向一張普通書(shū)桌:那是葉總的���。葉中敏女史時(shí)任《大公報(bào)》副總編����,以“關(guān)昭”筆名寫(xiě)時(shí)評(píng)專欄“井水集”�,金剛怒目,菩薩低眉���,我曾拜讀�����。聽(tīng)報(bào)館老人講�,她是從報(bào)館校對(duì)一步步做上來(lái)的�,很愛(ài)學(xué)習(xí),常與同事交流想法���,“真動(dòng)起筆來(lái)����,那可是倚馬千言?��!?/p>
我常去的香港中央圖書(shū)館��,館名大字遒勁�����,是前《大公報(bào)》副總編陳杰文先生手筆���。陳生供職《大公報(bào)》二十馀年,后去特區(qū)政府工作��。我家長(zhǎng)輩與他共事數(shù)年��,感佩不已:“他博學(xué)���、耿直��、坦率�����,待人平等�����,喜歡提問(wèn)���、討論,中英文俱佳�����?�!薄洞蠊珗?bào)一百周年報(bào)慶叢書(shū)》二○○二年出版�,我家有一套。陳生不但名列編審委員���,還設(shè)計(jì)了漂亮大氣的叢書(shū)封面����。
當(dāng)時(shí)年近九旬的李俠文先生��,人稱“俠老”�����,家中長(zhǎng)輩帶我見(jiàn)過(guò)他三次?�;貞浧饋?lái)�,總想給當(dāng)時(shí)的自己一掌:“就知道吃!”是俠老在灣仔附近山光道游泳后請(qǐng)便飯���。他像個(gè)慈祥的祖父���,問(wèn)我不少在校讀書(shū)之事及未來(lái)計(jì)劃?��;凇按笕苏f(shuō)話����,小孩不要插嘴”的理念�,我雖坐在俠老身邊,卻一心對(duì)付面前的牛排�。我那時(shí)的見(jiàn)識(shí),也不足以與他談?wù)撆f事����。如果能穿越回廿年前�,好想請(qǐng)俠老講講胡政之先生�����。俠老曾送我家長(zhǎng)輩一冊(cè)《胡政之先生紀(jì)念文集》�����,《大公報(bào)》百年報(bào)慶當(dāng)月內(nèi)部印行三百冊(cè)����,書(shū)名即由“李俠文敬題”�����。
一九四八年《大公報(bào)》港版復(fù)刊�����,是胡政之先生求存圖變的一著先手棋��。已是報(bào)社中堅(jiān)的李俠文隨胡先生來(lái)港主持復(fù)刊及編輯業(yè)務(wù)���。我見(jiàn)過(guò)俠老所繪“令箭荷花圖”�����,題字云此花為友人“移植海隅”后相貽����。《大公報(bào)》亦然��。一代又一代報(bào)人薪繼火傳���。
我不過(guò)一介旅客���,而香港無(wú)私,饗我以無(wú)償且優(yōu)質(zhì)的公共資源���,助我超越“此地此刻”的狹隘����,更令我耳聞目睹幾代人移植����、躬耕于海隅的盛況。一如書(shū)名“Living History”,一事發(fā)生�����,即成歷史�,人時(shí)刻活在歷史中。唯有博覽�����、勤行���、多聞��,才能真正在時(shí)間和空間的大荒中尋到依托���,找到自己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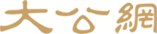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