離開(kāi)巴黎之前,我再一次去了塞納河��,這次去的是左岸��。面對(duì)正在整修的巴黎圣母院�����,沿岸一溜排開(kāi)十幾個(gè)鐵皮棚子��,出售舊書舊報(bào)和各類畫片�����。我愛(ài)舊書��,卻不懂法語(yǔ)�����,看些古意盎然的精裝本�����,捲邊泛黃的書頁(yè)�����,只能望書興嘆�����。于是��,把注意力轉(zhuǎn)向畫片和刊登圖畫的舊報(bào)刊�����,看圖解饞��。畫片內(nèi)容豐富�,尤以法國(guó)老建筑為多,水彩��、素描皆有��,絕大多數(shù)是印刷品���,也有手繪簽名的�����,只是對(duì)我的西洋美術(shù)史知識(shí)而言大大超綱���,無(wú)從辨識(shí)作者身份。在微涼的秋意里緩步前行�,只是單純感受巴黎、塞納河這份古意�。
走過(guò)一個(gè)書攤時(shí),忽然眼前一亮��。四五個(gè)大鐵夾子夾起數(shù)疊舊雜志�,懸掛在攤前。這些雜志同屬一刊�����,恰好我認(rèn)識(shí),是老資格的漫畫雜志《寒流》���,與《查理周刊》齊名的�。這本雜志創(chuàng)刊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愚人節(jié)��,二○○三年才改為彩色版�����。在這許多舊書中發(fā)現(xiàn)它們���,讓我有些放松,倒不是我喜歡這本雜志�,這就像仿佛參加一場(chǎng)聚會(huì),在滿眼生人中不經(jīng)意發(fā)現(xiàn)一個(gè)認(rèn)識(shí)的人�����,即便并不很熟甚至有些嫌隙�,但能叫上名字,也可以緩解陌生帶來(lái)的尷尬�����。
我取下鐵夾,拿下幾本舊刊來(lái)看���,發(fā)現(xiàn)都套著透明塑料袋�,想來(lái)賣家也是愛(ài)書人���。舊刊雖有十多本��,可惜不成套��,從上個(gè)世紀(jì)七十年代至近些年出版的都有���。我選了一本一九八八年出版的,付錢帶走�。拿著這本舊漫畫雜志,我走到不遠(yuǎn)處的莎士比亞書店打了卡�,又在幾家專賣漫畫和手辦的店里閒逛良久。漫畫是極具少年感的文藝���。慚愧的是�����,除了《丁丁歷險(xiǎn)記》�����,人到中年的我?guī)缀醵疾皇煜?����。但我推門而入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店員都抱以更多的微笑�。或許因?yàn)槲沂菛|方面孔�,或許因?yàn)槲蚁窠宇^暗號(hào)似地拿著一本《寒流》�。又或許,這所有“或許”只不過(guò)是我在塞納河左岸淘了舊書的心理作用��。(旅法紀(jì)行之十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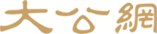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